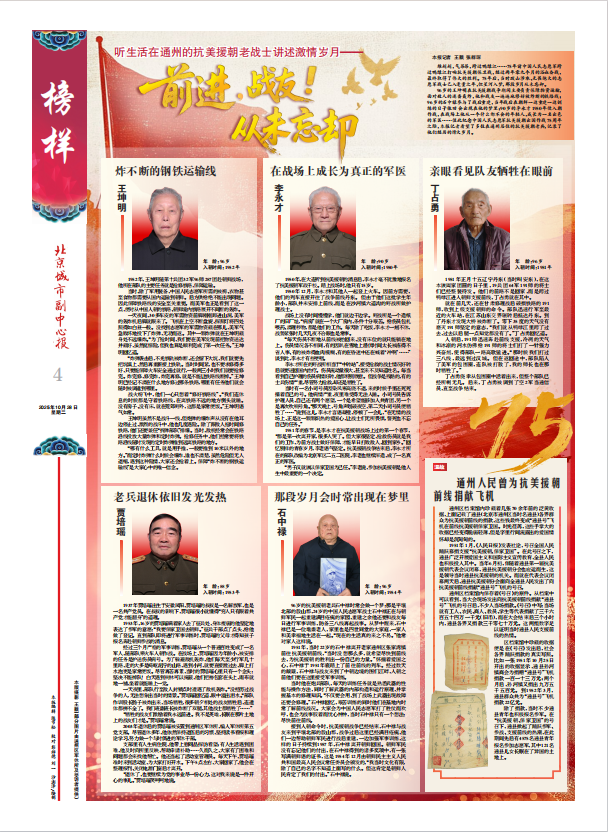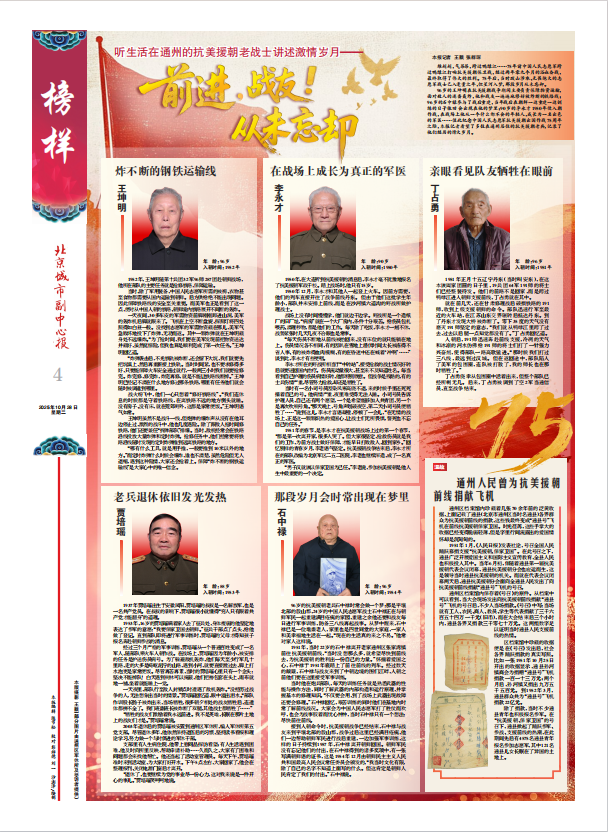
04版:榜样
本报记者 王戬 张群琛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75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打响抗美援朝保卫战,经过两年零九个月的浴血奋战,最终取得了伟大的胜利。75年后,当时跋山涉水、无畏炮火的志愿军战士已入耄耋之年,但星河入梦,那段岁月从未忘却。
96岁的王坤明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主要负责保障物资运输,面对敌人的连番轰炸,他和战友一遍遍地修好被炸断的铁路线;96岁的石中禄参与了战后重建,当年战后在朝鲜一边重建一边训练的日子依旧会出现在他的梦里;90岁的李永才1950年便入朝作战,在战场上他从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年轻人,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军医……值此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5周年之际,本报记者看望了多位在通州居住的抗美援朝老兵,记录了他们经历的烽火岁月。
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
王坤明
年 龄:96岁
入朝时间:1952年
1952年,王坤明随第十兵团32军96师287团赴朝鲜战场,他所在部队的主要任务就是抢修铁路,保障运输。
当时,除了军用装备,中国人民志愿军所需的被褥、衣物甚至食物都需要从国内运输到朝鲜。后方供给绝不能出现问题。因此保障铁路线的安全至关重要。而美军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便对从中国入朝的铁路、朝鲜境内铁路展开不间断的轰炸。
一天夜间,30多车皮的军需物资前脚刚刚卸进山洞,美军的轰炸机后脚就跟来了。飞机在上空不断盘旋,探照灯将四处照得如白昼一般。没找到志愿军的军需物资藏在哪儿,美军气急败坏地投下了炸弹,无功而返。其中一颗炸弹就在王坤明藏身处不远爆炸。“为了抢时间,我们要在美军发现前把物资送达并藏好,虽然挺惊险,但我也算是顺利完成了第一次任务。”王坤明回忆道。
“炸弹袭击后,不光铁轨被炸断,还会留下大坑,我们就要先把坑填上,然后再重新接上铁轨。当时时间紧,也不要求修得多好,只要能保障火车安全通过就行,一般两三小时我们就要抢修完。炸完修,修完炸,炸完再修,就是不能让铁路线断掉。”王坤明已经记不清在什么地方修过哪条铁路,哪里有任务他们就会随时被调遣到哪里。
战火纷飞中,他们一心只想着“修好铁路线”。“我们连休息的时候都是守着铁路线,在离铁路不远的地方倒头就睡。没有房子、没有床,就在荒郊野外,这都是家常便饭。”王坤明语气如常。
王坤明虽然不是战斗一线,但炮弹的爆炸声从没有在他耳边停止过,激烈的战斗中,他也几度遇险。除了跟敌人抢时间修铁路,他们还要兼任“拆弹部队”排爆。当时,敌机经常会在铁路沿线投放大量炸弹和定时炸弹。抢修任务中,他们经常要将铁路沿线随时发现的定时炸弹推到远离铁路的地方。
“哪有什么工具,就是用手推,一般要推到10米以外的地方。”而定时炸弹什么时候会爆炸,谁也不清楚,虽然危险但无人退缩,遇到这种险情,大家还会抢着上。保障“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是大家心中的唯一信念。
在战场上成长为真正的军医
李永才
年 龄:90岁
入朝时间:1950年
1950年,在大连听到抗美援朝的消息后,李永才毫不犹豫地报名了抗美援朝军政干校。踏上战场时,他只有15岁。
1950年12月,李永才和其他人一起登上火车。因前方需要,他们的列车直接开往了战争前线丹东。但由于他们这批学生年龄小,部队并未安排上前线,而是在沙河镇六道沟的野战所做护理战士。
战场上没有时间慢慢学,他们就边干边学。野战所是一个造纸厂的旧厂址,“病房”就在一个大厂房内,条件十分艰苦。给伤员包扎喂药、清理秽物,都是他们的工作。每天除了吃饭,李永才一刻不休,战势紧张时几天几夜不合眼也是常事。
“每天伤员不断地从前线被抬回来,没有床位的就只能躺在地上。伤员情况各不相同,有的因趴在雪地上潜伏时间太长被冻得不省人事、有的被炸得血肉模糊、有的在昏迷中还在喊着‘冲啊’……”谈到此,李永才有些哽咽。
李永才所在的野战所相当于“中转站”,接受抢救的战士情况好转后就要送回国内治疗。伤员流动量很大,甚至来不及知道姓名。每当看到自己护理的伤员病情好转,他都特别欣慰。但战争是残酷的,有的士兵伤情严重,尽管努力抢救,却还是牺牲了。
当时有一名小司号员因染风寒高烧不退,来的时候手里还死死攥着自己的号。他病情严重,夜里难受得无法入睡。小司号员告诉护理人员,自己还有两个愿望,一个是希望能够加入共青团,另一个是再次吹响号角。“那天晚上,号角声划破夜空,第二天小司号员便牺牲了……”说到这儿,李永才言语凝噎,停顿了一会儿,“在无情的战场上,正是这一颗颗炽热的爱国心,让战士们无所畏惧,誓死也不忘自己的任务。”
1951年的春节,是李永才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过的第一个春节,“都是第一次离开家,很多人哭了。但大家很坚定,抢救伤员就是我们的工作,为前方战士做好保障,才能早日打败敌人,回到家乡。”回忆别样的青春岁月,李老语气坚定。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李永才所在的部队改编为北京军区二五二医院,李老也继续深造,成了一名真正的军医。
“男子汉就该以保家卫国为己任。”李老说,参加抗美援朝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
亲眼看见队友牺牲在眼前
丁占勇
年 龄:96岁
入朝时间:1951年
1951年正月十五辽宁丹东(当时叫安东),在这本该阖家团圆的日子里,19兵团64军191师的将士们已经整装待发。他们的前路不是回家,而是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支援前线,丁占勇就在其中。
就在前几天,还在甘肃修理战后破损铁路的191师,收到上级支援朝鲜的命令。部队迅速行军至最近的火车站,在江苏山东交界辗转后抵达丹东。到了丹东才发现大桥被炸断了。零下35度的天气没有磨灭191师坚定的意志,“我们就从鸭绿江里跨了过去,过去以后腿一点知觉都没有了。”丁占勇回忆道。
入朝后,191师迅速奔赴前线支援,冷冽的天气和冰凉的河水仿佛给191师的将士们打了一针强力兴奋剂,使得部队一路高歌猛进。“那时候我们打过三八线,最远到过汉城。但在返回途中,部队陷入了美军的包围圈,连队被打散了,我的师长也在那时牺牲了。”
丁占勇侥幸从包围圈中活着出来,但整个部队已经所剩无几。后来,丁占勇被调到了空2军当通信员,直至战争结束。
老兵退休依旧发光发热
贾培瑶
年 龄:88岁
入朝时间:1953年
1937年贾培瑶出生于安徽凤阳,贾培瑶的叔叔是一名解放军,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在叔叔的影响下,贾培瑶很小就懂得“穷人只有跟着共产党才能翻身”的道理。
1953年,16岁的贾培瑶瞒着家人去了征兵处,身体瘦弱的他坚定地表达了参军的意愿:“我要保家卫国去朝鲜。”征兵干部点了点头,给他做了登记。直到部队即将进行军事训练时,贾培瑶的父母才得知孩子报名奔赴朝鲜参战的消息。
经过三个月严格的军事训练,贾培瑶从一个普通百姓变成了一名军人,随部队乘火车入朝作战。在战场上,贾培瑶因为年龄小,被安排的任务是护送伤员病号。为了躲避敌机轰炸,他们每天至少行军几十里路,走的大多是崎岖泥泞的山路,遇到小河,就要直接蹚过去,脚上打水泡更是家常便饭。尽管再苦再累,当时的贾培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坚决不能掉队!白天遇到树林可以掩蔽,他们把挎包套在头上,雨布就地一铺,坐着就能睡上一觉。
一天夜里,部队行至敌人封锁点时遭遇了敌机轰炸。“没经历过战争的人,无法想象出当时的情景。”贾培瑶回忆道,眼中溢出泪水。“部队作训股长肠子被炸出来,当场牺牲,很多朝夕相处的战友牺牲后,连遗体都拼不全了。我们班副班长被炸断了双腿,其他战士都牺牲了……”
“牺牲的战友们激励着我永远前进。我不是英雄,长眠在那片土地上的战友们才是。”贾培瑶常说。
2003年退休后的贾培瑶被安置到通州区军休所,编入军休所第五党支部。尽管退休多年,他依然保持退伍后的习惯,坚持读书看报和理论学习,努力做一个与时俱进的军休干部。
支部里有人生病住院,他带上慰问品探访看望;有人生活遇到困难,他及时向所里反映,帮助申请补助……久而久之,大家有了困难和问题都会来找他帮忙。他还当起了活动室管理员。每天下午,贾培瑶准时来到活动室,为大家打好开水。下午5点左右,大家回家了,他会在整理报刊、关闭电源门窗后才离开。
“退休了,也要继续为党的事业尽一份心力,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开心的事儿。”贾培瑶笑呵呵地说。
那段岁月会时常出现在梦里
石中禄
年 龄:96岁
入朝时间:1954年
96岁的抗美援朝老兵石中禄时常会做一个梦:那是平壤北部的殷山郡,24岁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石中禄正在与朝鲜军民一起重建满目疮痍的家园,重建之余他还要和战友每日进行军事训练,防备三八线再起战事。从梦中醒来,石中禄已是一位耄耋老人,家里也是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一家人和美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现在的生活真的来之不易。”他常对家人这样说。
1951年,当时22岁的石中禄离开老家通州区张家湾镇前往抗美援朝前线,“当时没想那么多,就希望尽快到前线去,为抗美援朝的胜利出一份自己的力量。”怀揣着爱国之心,石中禄于1951年底踏上了前往前线的列车。经过数天的颠簸,石中禄与战友来到了中朝边境的图们江畔,入朝之前他们要在这里接受军事训练。
当时他在炮兵部队,每天的训练任务就是熟悉武器的性能与操作方法,同时了解武器的内部构造和运行原理,并掌握基本的修理知识。“不仅要会用,到了战场上武器出现故障还要会修理。”石中禄回忆,艰苦训练的同时他们在基地内时常了解前线战况。大家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打了胜仗而欢呼,也会为战事胶着而忧心忡忡,当时石中禄只有一个想法:尽快前往前线。
接到入朝命令时,抗美援朝战争已经结束,石中禄与战友来到平壤北部的殷山郡,战争过后这里已经满目疮痍,他们一边帮助朝鲜军民进行战后重建,一边加强军事训练,这样的日子持续到1957年,石中禄离开朝鲜回国。朝鲜军民没有忘记他们的付出,在石中禄得到的诸多奖项中,有一张写满朝鲜语的证书,这是1954年12月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颁发的,“我当时文化有限,除了自己的名字不知道上面写的什么。但这肯定是朝鲜人民肯定了我们的付出。”石中禄说。
温故
通州人民曾为抗美援朝前线捐献飞机
通州区档案馆内珍藏着几张70余年前的泛黄收据,上面记载了通县(北京市通州区当时名通县)各界群众为抗美援朝前线的捐款,这些钱最终变成“通县号”飞机在前线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时光荏苒,这些手掌大的收据已经变得脆弱轻薄,但是字里行间流露出的爱国情怀却是沉甸甸的。
1951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全国人民踊跃募捐支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在此号召之下,通县广泛开展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宣传教育,全县人民也积极投入其中。当年6月初,伴随着通县第一届抗美援朝代表会议闭幕,通县抗美援朝分会也应运而生,这是领导当时通县抗美援朝的机关。而就在代表会议闭幕两天后,通县抗美援朝分会面向全通县人民发出了向抗美援朝前线捐献“通县号”飞机的号召。
通州区档案馆内保存着《号召》的原件。从档案中可以看到,当大会现场发出向抗美援朝前线捐献“通县号”飞机的号召后,不少人当场捐款。《号召》中写:当场就有工人、农民、商人、教员、学生等代表捐献了三千六百五十四万一千元(旧币),而在大会结束后三个小时内,通县各界又捐款三千零七十万元。这两组数字足以证明当时通县人民支援前线的热情。
区档案馆中珍藏的收据便是在《号召》发出后,社会各界踊跃捐款的真实写照。比如一张1951年10月25日开出的收据显示,通县孙河镇商会为捐赠“通县号”飞机捐款一百一十三万元;两个月后,孙河镇又捐出九万五千五百元。到1952年3月,通县群众共为“通县号”飞机捐款22亿元。
除了捐款,当时不少通县青年也积极报名参军。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下,通县掀起了踊跃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的热潮,在此期间先后有4575名通县青年报名参加志愿军,其中121名通县儿女长眠在了异国的土地上。